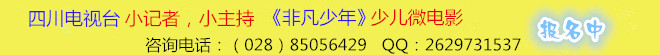|
作者: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四年级三班 吴佳音
我妈妈早产的缘故,我小时候就长得瘦瘦小小,尖尖的脸,还扎着高高的马尾,因为家里人都要工作乏人照顾,妈妈自小就是祖祖拉扯大的,在妈妈的眼里,祖祖永远都是颤颤巍巍的,时不时紧紧抿嘴唇;或者在灶台下拉着被熏得乌黑的风箱弄吃的,或者背着一个比她身体大许多的筐在田里挖挖刨刨。在灰黑色的泥路上,她矮矮的身影,蹒跚着融入那昏黄的光影里踽踽独行……
大概在我妈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她的大伯因为车祸不幸离世。仿佛晴天霹雳,祖祖惊悉这一消息悲痛万分日夜以泪洗面,生生的哭瞎了双眼,自此以后在家里就只能以手代眼,摸索而行了。那时家人工作的地方极远,照顾祖祖的重担就落在了年幼的妈妈肩上,祖祖大约是人老睡得少的关系,向来起来得极早,所以妈妈经常要天不亮就要起来熬稀饭,熬好了端到祖祖常坐的方桌的右下角,方便她用手就能摸到,还得提前五分钟放好凉着,这样祖祖突然摸到的话也不会烫手,可以慢慢小口小口的喝着。 妈妈中午放学后,就要匆匆忙忙跑回家做午饭,因为人矮的关系,常要拿一个小凳子放在灶前站上去才能够方便炒菜,锅铲对于她来说有些沉重,要双手拿着才能把菜翻得均匀,一个小菜都能炒得满头大汗,还常常因为气力小手短,烫着摔着是常事。难得妈妈小小年纪却从不怨怼,也不曾和人提起…… 也许是太老的缘故,祖祖面上几乎皱到了一块,从额头到鼻子没有一处平的地方,牙齿也几乎掉光了,嘴始终那么向内凹着,平时不吃东西似乎也在慢慢一瘪一瘪的动着;头发慢慢稀疏,渐渐地没法完全遮住,露出一小片一小片头皮。皮肤像久旱龟裂的土地,干枯而失去弹性,灰褐色的老人斑大片大片像锈蚀一样布满全身。在身边的话,还会隐隐约约闻到一股味道,像泥土的腥味,没错,那就是人慢慢腐朽渐渐老去的味道…… 时间来到了2003年的夏天,堪堪到了七月半,这天的晚饭,祖祖出人意料地吃了两大碗稀饭,饭后还郑重其事地要求大家全部留下来,然后开始念念叨叨的说什么爷爷又来看她了,如果有什么不妥,她会安安静静悄悄离去,这半年以来祖祖似乎是神智不大清醒的缘故,常常说一些神神叨叨不知所云的话,大家明白她年纪大了许是是有些糊涂,也没怎么往心里去,照例笑着安慰她几句。没想到祖祖竟然一语成谶,当晚就过去了,待清晨发现的时候,整个人都蜷缩成小小的一块了!大人们怎么也无法拉直,妈妈哭得泪人似的,一边低头轻轻地抚摸祖祖的手肘,一边低头在她耳边说着什么,难以置信的是,过了一会儿,祖祖手竟然慢慢地伸直了,干瘪的眼里渗出泪来,缓缓的在脸颊上蜿蜒滑落。仿佛即便是阴阳永隔,她们之间仍然有一种神奇的心灵联系,无法割断,难以阻隔……
这种神奇的联系也似乎存在于我和妈妈之间,由于好吃的缘故,我生得矮矮胖胖,妈妈常笑我“假若削肉十斤,便是百里挑一”,我脸圆圆极普通的样子,属于丢到人海里也翻不出一朵小浪花的那种人,但很神奇的是,无论是上学时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路口;还是放学时吵闹喧嚣人头攒动的东小门外,我只要走出来抬头四处张望,妈妈就会第一眼看到我。我甚至猜想就算我变成小鸟从她头上掠过,她也会心有所感抬头张望吧。我曾经带着疑惑问起这个,她楞了一下说:“大概是感觉吧,具体说不清楚,就是觉得你会在那里啊。”我听了哈哈大笑,眼睛直直看着她,就在那一刻,我们的眼光被什么仿若实质的清亮连在一起,永远也无法分开。 |
新闻热线:4000-2300-35 QQ:516396333